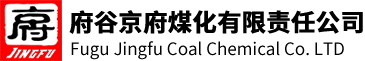11
2021
-
11
酸白菜,那牵动着的情思
酸白菜,那牵动着的情思
李琴
又到腌酸白菜的季节了。看着那一网袋绿白相间,鲜嫩圆润,一攥出水的大白菜,竟然有点儿不知所措。为了能腌制出酸而不咸,清新爽口,软中带脆,色泽金黄的酸白菜,足足在网上翻阅了不下十遍腌制酸白菜的视频,可心里头依旧七上八下,一直在打鼓,终究还是没个谱。视频上虽然有白开水烫菜的细节,有撒盐的过程,可大白菜在热水里该浸泡多长时间,该撒多少盐,依然还是个未知数。腌菜高手们凭的是多年的实践经验与自我感觉,我一没经验,二没感觉,靠得就是稀里糊涂。不是有句话说“难得糊涂”么?活得糊涂点儿,大概幸福会来得容易一些。活得太过明白了,反倒被鸡零狗碎折磨的苦痛不堪。只是这腌制酸白菜,到底还是和做人和活法有些异同。糊涂也好,明白也罢,想来还是不能得心应手。所谓不能得心应手,不是腌制的不好,也不是纯粹的不会腌制,是介于会与不会之间的说会不会,说不会还稍微会点儿的半瓶瓶醋。说完全不会,有点儿虚假!毕竟50多岁了,吃酸白菜也不是三天两天,又不是十分讲究技术含量的活儿!说会,又真的感觉有些为难,为难到不好意思启齿。因为这半辈子,独自腌制酸白菜的次数少之又少,想想也就一两回,最多没超过三四回,其实说穿了,前半辈子就是个甩手的二掌柜。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日子过了几十年,是因为有一个事无巨细、任劳任怨的老妈妈。老妈妈三十三岁上生的我,我上面有两个哥哥,大哥比我大十岁,二哥比我大六岁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应该是伴随着糖豆豆出生的,就是从嘴上甜到心里头的那种甜,甜得不能再甜、甜得要发腻的那种甜!那个时候,家里虽没有债台高筑,却也够得上一贫如洗。穷的叮当响的家,靠着水煮白菜帮子度日充饥的家,却把我这个唯一的女儿,唯一的妹妹,宠得快要上了天!母亲在世时常和我叨啦,说我刚会坐还是会爬那会儿,大概是七八个月、八九个月的时候(我记不太清楚了),妈妈把我放在炕沿边,她站在炉台跟前做饭,我可能是刚学会坐着摇的本事,亦或从小就爱“显摆”的缘故,特别稀罕这摇呀摇。摇呀摇,摇到外婆桥,外婆桥没摇到,一不小心就摇到了地下,把正在喂羊还是扫院的二哥吓得不轻。听见哭声,他拿着扫帚,追赶着邻居家的黑毛猪,就是一顿猛打,边打边还叫骂着:“就你把我妹妹闪哈地的”。我听着母亲说这些陈年趣事,一阵阵暖流涌上心头。小时候的二哥是何等的疼我惜我,时至今日想来,依然余情满满,温暖如初···
在同龄人中,我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,是别的小娃娃们羡慕的首选对象。他们羡慕我,不是因为我们家有钱。那个时候,家家每每基本一个样儿,就是一个谁都不爱听也不愿提的字——“穷”。穷,是那个时代的特征,那个时代的标志。对于如今含着“金钥匙”长大的孩子们来说,他们几乎想象不出我们那个时候的穷样子,和他们念叨当年贫穷带来的诸多尴尬,他们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,轶趣奇闻。那年那月那日子,菜里头几乎见不上个荤腥汤汤,饭里面也难得飘多少黄油花花。桃黍米大饼子烩酸白菜,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吃喝。我们家那时候腌酸白菜,不用热水煮,只把白菜洗净,撒上适量的盐,放在大瓮中自然发酵,撒盐的过程看似简单,实则不然,盐一定要一层一层均匀地抛撒,否则,存放时间不会太长。过罢年二三月,天气渐渐暖和,白菜酸得溜溜间,即使不放油不放盐,用清水煮上,在那些年也是相当不错的饭菜。那时候村里走出来的人,不是拇指头粗的脖子上挑着个小脑袋,就是瘦的眼睛蓝凹凹间(wa),眼珠子白寡寡的,头皮上的青筋突突地跳,完全一副饿民形象,哪有现在腰肥体壮,营养过剩的帅哥靓妹?像高血糖,高血脂这些如今极为普遍的富贵病,在那个年代属实罕见,几近闻所未闻。贫穷,限制了想象,也限制了思维。但是我,却在穷困潦倒中享尽繁华,享尽疼爱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总也忘不了父亲背着我上学的情景。
当年,我背着母亲手工缝制的书包,父亲背上背着我,捎带着手里还拿着干树枝和洋火,送我到学校。到了学校,父亲把我放在座位上,再把教室里的洋炉子烧着,然后才放心地离开···父亲于我,有着太多温暖的回忆,就像我在《我的父亲》中写到的:“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,也是伟大的。他的平凡是因为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,伸着粗糙的双手没有地位操劳了一辈子;他的伟大在于不仅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,给了我们精彩的生命,而且还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尽量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,将他那深沉博大的父爱,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。”我更忘不了课间操的二十分钟,偷跑着回家,一进门就喊妈妈,喊着:“妈,我饿了,我饿了。”然后,迫不及待地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菜,再跑去学校上课······我在贫穷的年代,贫穷的家庭里,享受着富足的宠溺与关爱。因宠及爱,因爱及福,这份情如今想来依然热泪盈眶,依然感慨万千。
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羡慕我,是因为我享受着别人享受不到的疼爱。闺蜜从小没娘,曾经无数次地和我说过,我小时候是如何如何的幸福,如何如何的快乐,如何如何的随心所欲。在她幼小的心灵里,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都在渴望着得到父爱与母爱,把父母的疼爱当作奢望,当作施舍,当作永不可攀的高贵。她说,一起玩过家家,我永远是那个高傲的富家小姐,她永远是那个侍候我的丫鬟,她把自己贬到最低。好在,如今她终于活成了人上之人。偶尔回想起这些,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着泪光,神情悲切忧伤,为她早逝的亲娘,为她没有得到的母爱。
前几天,和墙头的同学去野地烧三也、烧红薯。一个叫云云的女生说,她初中时常去我们家,看见我妈亲我亲的她羡慕的不得了。她的父母早年离异,她是在残缺的家庭中长大的娃娃,受尽了欺凌,受尽了辱骂,受尽了白眼,从来没有得到过来自家庭的丝毫温暖,有的只是冷漠、冷眼、冷嘲。她说,上初中那会儿,社会上刚流行戴手表,全班没一个有表的,只有我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电子表。那块电子手表现在看来并不金贵,只值区区的五块钱。可在八十年代,五块钱是个什么概念?那时候一个碗托一毛钱,五块钱就是五十个人吃碗托的总和,而那五块钱的电子手表,则是我的大哥省吃俭用给我买的。哥哥那时候在县医院上班,工资并不高,一个月大概也就三四十块钱,却给我买了当时来说最昂贵的奢侈品。我的优势并不是我家有钱,而是家里只要有一块钱,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、我的兄长,都会花在我的身上。同学羡慕的不是我贫困的家庭,而是贫困中能时时满足我愿望的家庭。
母亲从我记事起,就在我的耳畔悄语,我是她的命心心,是她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。在我的印象里,母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发型,没有买过几件像样的衣服。她永远都是齐耳的短发,白皙的面庞。母亲的短发,从来都是齐齐整整地梳在耳朵后面,记忆之中,母亲的头发都是自己照着镜子修剪打理的。母亲在那个年代是不求人的,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,在村子里不受人待见,母亲因着这事还陪父亲在戏台子上挨过批斗。直到后来搬至县城,在我的几番要求之下,母亲才开始出入理发店。母亲最后一次进理发店,也是她去世的当天。那是2017年的7月26日(农历闰六月初四)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。那天天很热,树叶都被晒得打了卷儿,空气中弥漫着的热浪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刚回到府谷,就在二道街碰上去理发的母亲。母亲对我说,她的头发长了,热的不行,理发个呀。母亲没有一点点要去世的迹象!就和平时一样样的。她又说,你大在家看电视了,你回个哇。本来我是准备和母亲去理发的,可她却说,你忙你的,我一个人能行了。我便没再坚持。由于我的没再坚持,让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与愧疚,让我在四年以后的今天都难以释怀。就在那天晚上,母亲冠心病发作去世了;就在那天晚上,我永远永远失去了疼我爱我、视我如珍宝如生命的人。
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,从小没上过一天学,她认识的所有字,都是结婚以后在扫盲班里学到的。母亲的记忆力特别好,称得上过目不忘,她能够把村子里大多数人的生日毫无差错的说出来。姥爷姥娘重男轻女的思想极为严重,舅舅们基本上都是初小高小、甚至师范院校毕业,而母亲,却连上学的机会都不给。我常想,母亲如果像我这么念书,是不是就能成了大学问家?或许,真如人们所说,人不得个全,马不得个辕,想要追求完美的生活,几乎没有任何可能。母亲的五官不花哨,但很耐看,父亲曾说,母亲年轻时候是个美人,或许这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的缘故。不过我也觉得母亲很美,亦或这又是应了那句“儿不嫌母丑”的古话。儿真的不嫌母丑!哪怕是个奇丑无比的妈妈,只要活着,只要健康,也能有个盼头,有个走处,有个遮风挡雨的家!有个受了委屈可以流泪的地方!只是这些,我已经没有福气享受了。
母亲在世的时候,我从来没有为腌制酸白菜操过心,因为轮不到我操心。每年到了腌菜这几天,母亲便和父亲一趟一趟往家里买菜,偶尔我回去要帮他们,母亲也总是说,你忙你的,我和你大甚也不做,我们买呀。我看他们一趟趟往返,乐此不疲,也不再理究,想着让他们做些琐碎营生,他们会觉得自己虽然老了,在儿女心目中依然大有作为。在母亲最后生活的那几年,租住着亲戚家的房子,那是头道街和二道街中间的小独院,前面是几家单位的办公室,府谷人把那里称作“联合国”。由于紧邻超市、医院、菜市场,生活极为便利。当时的集市还没有搬迁至如今的农贸市场,逢一逢六的集市,设立在二道街。到了过集这天,二道街上熙来攘往,好不热闹。农副产品,日用百货,琳琅满目,堆积如山。母亲在二道街的集市上来来回回,已经成为她最大的乐趣。离集市几十米远的父母家,是我们兄妹三人的落脚点。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有父母的日子,习惯了一家人其乐融融,围坐在一起吃饭拉话的日子,习惯了有父母操心的日子。只是这种日子,在母亲去世后消失了,就像逝去的母亲一样。
前几天给嫂嫂打电话,问询腌制酸白菜的事,她说我要吃就给我腌了,我要不吃,她就不腌了。嫂嫂,依然还是以我为中心的那个嫂嫂,我真的好感动。老嫂如母,嫂子也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,我不再好意思麻烦她给我腌酸白菜。如今我也为人妇为人母,并且当上了婆婆,自己该做的营生终归要自己来做。父母亲去世后,嫂子一如往常,依旧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邀约我回去吃饭,只是,嫂嫂叫我十次,我最多也就回去两三次。我再也找不到父母在世时全家团聚的那种感觉,那种氛围。有时候拒绝过后又很后悔,毕竟,于我而言,最亲近的只有两个哥哥了。
在这世上,用生命疼爱自己的人,只有父亲和母亲。父母在,家就在;父母不在了,家也就没了。生活,在突然之间变得很沧桑。没了父母的自己,如同一棵草一样无助、无奈。生活,虽然遍体鳞伤,如牛负重,但依然在周而复始的行进着;生命,自强不息,朝气蓬勃,简简单单的延续着。只是那酸白菜的情结,却一直牵动着我的心……
李琴,女,出生于陕西省府谷县墙头村,毕业于榆林卫校。自幼酷爱文学,曾在市县级刊物发表过多部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