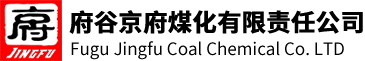28
2022
-
02
春节印象
犹记得儿时春节的前一两天,家家户户都会忙着贴春联。那时候春联都是买几张红纸自己写。爷爷写得一手好字,每到春节,就是爷爷挥毫泼墨,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刚写好的对联,墨迹未干,铺在炕上,屋子里便飘溢着浓郁的墨香。还是孩子的我特别开心,总是等不及对联干透,便要刷浆糊,出去贴。爷爷家、自己家,两进院,贴一天也不觉得累。临了还得再裁个小小的纸条,拿起笔来歪歪扭扭的写上四个字——天天下蛋,出去贴在鸡窝旁,美滋滋的盼望着一年的鸡蛋能够可了劲的吃。
贴了一天对联的小手,冻得发红,手心里全是浆糊和墨迹,夹杂着对联上的褪红。站在院子中央,环顾四周,满满当当的红色,充溢着节日的喜庆,自得之意更是不言而喻。写完自己家的对联,爷爷也会帮村里其他人家写,一忙就是一整天,每当别人以礼相谢时,爷爷都会笑着婉拒,他说,乡里乡亲的写几个字的事儿,不必客气。只有送别亲邻后,才会揉着发酸的手腕,显露疲态。
故乡有风俗,除夕下午总要堆个火龙,做个旺火,图个年年兴旺,代代发达。比较讲究的人家,旺火能堆个1米多高,堆在院子中央,规规整整,特别气派。自家虽然不细讲究这个,但也弄的差不多哩。小时候爱掺合这个事,大人们垒,我帮着打炭,折柴棍,忙乎半天也不累不烦,觉得有意思极了。甚而还总要捣乱垒两块炭,想垒高高,但总也垒不稳当,难免有些灰心。便由大人们去弄了。
除夕夜在院子里放炮,火龙的旺火冲天,照的院子通明。天上的烟花绚丽,四下里都是光明,孩子们的欢笑声,村落里的爆竹声,屋里的春晚声,从晚到明不曾稍停。红红火火过大年,大概便是这个样子吧。
对于孩童来说大年初一,最是开心。大清早起来,赶紧先穿一身新衣服。接着便是出行,出行是大事,有讲究有条件的人家总要去远方拜庙。更多的是自己问个风水先生,明了祭祀方位,端好先祖牌位,拿着一应糕点贡品、香箩纸炮,便带领一大家子去田野出行。到地后,拾薪点火,八方位放炮,以供先祖,以敬神灵。小孩子不懂这些,只顾着四处放炮,就爱听那两声响。到处捡些特色石头,或有稀罕,能有古铜钱,这便是“捡元宝”。代表着一年的财运 其实小孩子的我哪管什么财运,只是觉得捡石头有意思,不觉得风寒,不知道雪冷。总要大人们忙完,招呼着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。路上仍要跑着再捡几块才行。
归来后,便要向爸爸妈妈拜个年,讨要红包,拿到手后就不理他们了,自顾去爷爷家,一进门便叫喊着“爷爷奶奶过年好,我来拜年了。”径直走到身边,手就展展地伸出来。爷爷有时装不懂,那我也有招,上了炕,拱到怀里,装模作样磕头,说几句调皮话,惹得爷爷哈哈大笑,掏出早已备好的红包来。
略坐一会,便要嚷嚷着哥哥带我出去玩,那时候村里的小伙伴极多,这家进,那家出,唠嗑,打牌,呼朋唤友四处游荡。开饭时,村里四处响起这家妈妈那家奶奶叫自家孩子回来吃饭的声音,这声音极亮,响彻了村里村外,响彻了各个节假日,更是响彻了我的童年。
如今,春节不曾回,在视频中给亲人朋友拜了年。工作之余,抽空与母亲聊天,得知过年回家的人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一辈,儿时的小伙伴大都在外,本该红红火火的春节此时却显得稍加冷清。对联一事,人在单位,不曾亲手贴,更没有亲手写,家中爷爷年迈,封笔已多年,父亲不再得闲,零零散散买了几副对联,偌大的两进院落,只是有个对联罢了,散落着几点点红色,也就是略有个意思。
至于火龙旺火,多年不曾好好弄,今年又添炭价大涨,我问父亲,又是碗大的火龙?父亲笑着点头没说话。初一出行的仪式,不知不觉中竟已废弃多年,田野里篝火不再燃起,炮响声也不再回荡,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。久在他乡总是念着故乡的风俗,除夕夜问父亲出行的方位,才知早已无人弄这些了,出行的方位更是无人知晓。言罢颇感遗憾。故乡的小伙伴们早已各奔东西十几年,大多失去了联系。
哥哥今年春节在家,初一不曾串门,他的小伙伴过节也无人回。村里不见了放鞭炮的孩童,星夜只有烟花零星升起。不闻欢笑声,若不是手中的手机,或许不知过年。年与时驰,意与岁去。记忆中的往事越发清晰地浮现在心头,而我却离那个美好的童年越来越远了。
陈麒栋,府谷人,于文学自幼有些偏好,喜欢用文字记载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人,那些事,或悲或喜,唯有真情实感以动人心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