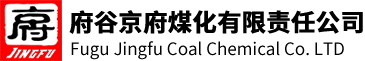20
2022
-
06
李琴丨我的父亲
我的父亲
今天又是父亲节。
独自坐在办公桌前,望着朋友圈里刷爆了的有关父亲节的礼赞与祝福,眼泪像一股流淌着的清泉,缓缓的缓缓的,顺着脸颊,顺着下巴,一道道,一道道地滴落在地面上--
曾经,在一个父亲节的时候,我写了一篇《我的父亲》,发表在府谷文学的平台上,后来又被转载于当地某刊物,并且得到了200元的稿酬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!兴奋、激动、欢喜的心情不言而喻。
记得当时拿到稿费,我迫不及待地去了母亲家中。一进门,就炫耀式地把崭新的200元钱给了母亲,然后又把杂志翻开,递给沙发上乐呵呵看着我的父亲。那时,我是何等的得意,何等的自信,又是何等的骄傲!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也终于把我朴实的老父亲,用我朴素的语言,朴素的风格,有些笨拙地写了出来,并且永永远远留在了记忆的长河里。
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厚良善、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在父亲八岁的时候,他的母亲,我的娘娘(奶奶)就不幸去世了。没过多久,家境殷实的爷爷,便娶回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漂亮的小寡妇,并且还带来一个比父亲小六岁的女儿。那一年,爷爷42岁,父亲还不到9岁。他们父子没有如小说中所描述的“相依为命,患难与共”。因为爷爷手里有钱,无需和儿子患难,大概也觉得没有多少必要在乎他唯一儿子的感受。据邻居大娘娘说,父亲在失去他的母亲之后,大多数时间吃住在何姓奶妈家,好像奶妈一家才是他的安慰,他的亲人。即使偶尔回到他生活了八年的家中,也是很短暂的停留,极少在那里过夜。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,大都看见过年幼的父亲,在失去母亲之后,常常睡在戏台子上,仿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。父亲在世时,我曾经好多次问询过父亲个中缘由,问他为甚不回家?为甚要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睡觉?但父亲每次总是有意无意地岔开话题,不置可否,甚或一笑了之。他从来也没有在我和哥哥们面前提到过他的后妈,我的新娘娘。有关新娘娘的一切,都是从我的邻居大娘娘嘴里,断断续续地听到的。尽管父亲从未提起过我的新娘娘,但我知道,逢年过节,父亲总是会去河曲县的巡镇,看望早已在爷爷去世后再次改嫁的新娘娘。那个年代,车是极为罕见的奢侈品,几十里路上步行往返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从我记事起,年头节下,父亲看望新娘娘的习惯就从未改变过,一直到新娘娘去世才终止。
父亲生前对我说的最多的事,就是我的娘娘在世时,他们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。想来,那时候的父亲,绝对是幸福的,更是快乐的。每年的八月十五,娘娘早早儿就做好了月饼,然后拿出一部分,放到一个大坛子里,倒上酒,像农村醉枣儿一样,盖上盖子,随吃随取。父亲说,娘娘给他醉得月饼能一直吃到腊月。沾了酒的月饼酥软香甜,就像父亲的童年一样,回味无穷···小年后,家家户户都在炸麻花,炸茶食,殷实的娘娘家自是不例外。这样,父亲一年到头几乎零食不断。在当时,算是极为奢侈的了。父亲还说,那时候最好吃的饭菜,是山药豆腐汤汤饭。他和爷爷都特别爱吃,于是,娘娘隔三差五的总要给他们做得吃,直到娘娘三十六岁时难产去世......父亲在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,似乎依然沉浸在对娘娘深深地怀念之中。而我虽然没有见过娘娘的面,内心也感到万分酸楚,为我可怜的父亲,也为我早逝的娘娘。
父亲性格内向,为人特别谦卑,行事又格外低调,或许,这与他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。父亲在九岁的时候,就被爷爷送到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家私塾里念书。那时候,是真正的“念”书。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开始,先认字、后背诵,而后用毛笔书写。父亲在这家私塾里念了七年书。老师是一个姓王的本地先生,在给他们教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的时候,从来不解释意思,只是要求他们背诵句子。这些文言文对于八九岁的孩子来说,相当晦涩难懂。我问父亲,他当时能否理解其中的意思,父亲说他完全不懂,是靠死记硬背才不至于挨板子的。和他一起读书的还有好多村子里的娃娃,不少人经常挨打,手指头常常肿得握不住笔(我现在会背《三字经》中的一些段落还是得益于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的)。他们在背诵之余,最主要的是认字练字。父亲天资聪慧,勤奋好学,又踏实认真,所以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并且是双手都能写(父亲是左撇子,老师让右手练字,后来左右手就都会了),这在村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,在我们家却已经不算是秘密。
特殊的家庭使得父亲过早地熟知了世事。十七岁那年,父亲被爷爷派去后套给他换洋烟,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。民国时期,河套地区(俗称口外)盛行种洋烟,不仅周边十里八村的村民因此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,就连我们口里的有钱人也难逃厄运。可怜的父亲慑于爷爷的威严和继母的冷漠,独自赶着老黄牛车,从家里拉着糜子,豆子这些,星夜兼程,赶到千里之外的大河套……在当时,走西口对于一个大人来说,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何况一个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,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父亲知道。而他却极少提起这段经历,不知道是不愿意说,还是真的无话可说。
父亲在流失的母爱中渐渐长大成人。他和我的母亲结婚后,成了远近闻名的种地好把式,村里没有多少人还记得父亲曾经是私塾里的优秀学生,只有他的老师偶尔在遇到父亲的时候,会很遗憾地摇摇头,表示十分的惋惜。土改那一年,父亲的命运有些转机。当时在村里,像父亲这么有文化的人,屈指可数。于是,经村委会研究决定,让父亲当文书。然而,时间不长,就有人揭发,爷爷是富农,父亲是富农子女,富农子女哪能在文书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工作?父亲就这样被残忍地剥夺了仅有的一点点尊严,再次拿起锄头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默默守护着自己名下仅有的那几亩薄田,过着皱皱巴巴的穷苦日子……
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父亲因为爷爷的富农成分,挨了不少批斗,还因此连累了我善良的母亲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母亲每次说起她挨批斗的事情,都会数度哽咽,泪流不止。姥爷家是中农成分,不富裕也不贫穷。如果母亲不是嫁到这个曾经一度辉煌,最后又极度贫穷的破落家庭,哪能让造反派拉去批斗?母亲的委屈可想而知。在母亲痛哭流涕诉说这一切的时候,父亲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默默地把我抱在怀里。父亲本身就不是个善于言谈的人,不会解释,更不会安慰母亲,只能无奈地忍受爷爷给他带来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。那时候的我,虽然少不更事,但看着母亲伤心,我也便非常痛恨从未谋面的爷爷。不管怎么说,是富农爷爷连累了我的父亲,让父亲戴着“地富反坏右”的帽子,处处受人白眼,遭人排挤。甚至连品学兼优的哥哥,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,也因为富农的帽子,与当年的选拔上高中无缘,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升学的机会,成为全家人的遗憾!曾经发生的这一切,在后来和母亲的闲谈中更加真切地感受与认知过。或许,有些经历,总是难以忘怀的。比如,苦楚;比如,困难。但父亲,却从来没有在我们兄妹面前提起过什么,更没有计较过什么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父亲依旧任劳任怨,坚守在家乡这片贫瘠的土地上···
十年动乱后,父亲头上的帽子,终于不明不白地移除了。没有人给他平过反,也没有人追究过他的富农帽子是否还应该继续戴着。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稀里糊涂,就这样本本分分,就这样紧紧巴巴,亦然而然地过着我们的日子。这样的光景,大概持续了五六年,在一次村民选举中,父亲竟然被光荣的推选为生产队长。原本老实敦厚、慈祥和善的父亲,一下子被重视,突然有种闻宠若惊的感觉。父亲似乎愈发地勤劳了。他带着队里的人们,从包产到组,到包产到户,沿着农村改革开放的脚步,一路走来···日子过得越来越宽裕,越来越舒心。
从七八年到八二年,两个哥哥先后考上了中专,父亲似乎一下子成了村里被人尊敬的人物了。人们羡慕父亲教子有方,也有人感叹世道变化无常,“地富反坏右”的子女竟能登上高等学堂,这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!那段日子里,家里每天晚上,都聚集了不少出工回来闲聊的人们。平时想走近的也不再顾忌父亲的成分,和父亲拉话,给他递烟,再也不把他当成异类了。父亲很自然地接受着这一切,还像从前一样和蔼可亲,谦逊待人。
弹指一挥间,二十几年过去了,父母亲的年龄渐渐大了。哥哥们便商议着让父母搬到城里,帮着我们带孩子,顺便也享享清福。然而,勤劳惯了的父母亲,不习惯县城里太清闲的生活,他们相跟着,一趟一趟地从河边,把土担回来,铺在院子的周围,种上瓜果蔬菜。等到这些瓜菜成熟以后,父母亲又迫不及待地给我们送在家里···那一幕,如今想来,依然感动到泪湿衣襟。父亲甚至在无聊的时候,会到街上捡纸片子和饮料瓶子。刚开始我们兄妹都很尴尬,尤其是二哥,非常强烈地制止过好多次,但仍然无济于事。固执的父亲根本不听我们劝阻,完全沉浸在他成就感十足的喜悦当中……
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父亲虚龄八十六岁了,身体已大不如从前,母亲当时也已经八十岁了,并且患有较为严重的“三高”和冠心病。我们兄妹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,除了中午哥哥嫂嫂去给父母亲做一顿饭以外,其余时间,都是父亲一直在陪伴着母亲。父亲依然少言寡语,但对母亲的关心却有增无减。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盘子里或者父亲的碗里,只要有一块瘦肉,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夹到母亲的碗里。母亲由于疾病繁多,一年四季不能停针停药,而她自己又常常忘记打针吃药。于是,按时按顿吃药打针,便成了父亲督促母亲的头等大事。数年如一日,从未间断,从未改变。父亲的坚持,让我几度动容落泪;父亲的付出,令我百感交集。就像西式婚礼中的誓言:“无论富贵与贫穷,无论健康与疾病,都能不离不弃”。父亲从未给过母亲任何承诺,但他所做的一切却让母亲无不心安。女人一生,有着如此深情的陪伴,夫复何求?母亲年轻时虽然吃过不少苦,但能拥有父亲一生的关爱,该是多么的幸福与幸运!
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,也是伟大的。他的平凡,是因为他和全天下朴实的农民一样,伸着粗糙的双手,没有地位地操劳了一辈子;他的伟大,在于不仅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,给了我们精彩的生命,而且还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,尽量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,将他那深沉的、博大的父爱,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。父亲淳朴善良、宽厚仁慈的性格与勤劳节俭、踏实认真的生活作风,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他始终是我们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好父亲!
父亲,我们永远怀念您!